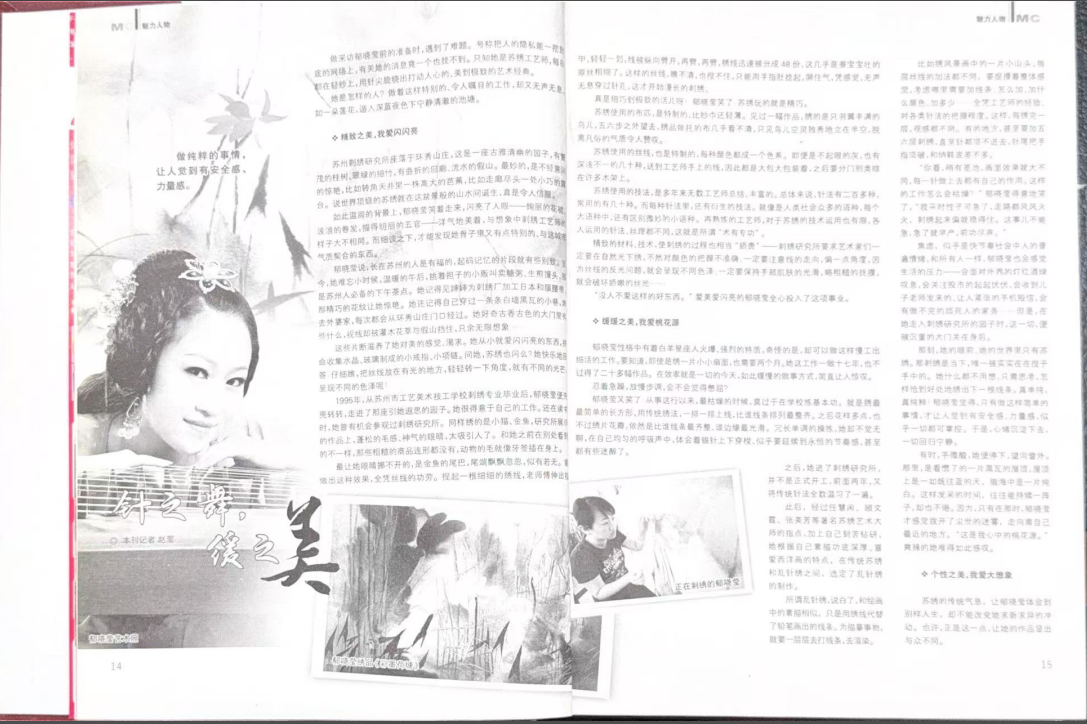
做纯粹的事情,让人觉到有安全感、力量感。
做采访郁晓莹前的准备时,遇到了难题。号称把人的隐私能一挖到底的网络上,有关她的消息竟一个也找不到。只知她是苏绣工艺师,每日都在轻纱上,用针尖旋绕出打动人心的、美到极致的艺术经典。
她是怎样的人?做着这样特别的、令人瞩目的工作,却又无声无息,如一朵莲花,遁入深蓝夜色下宁静清澈的池塘。
精致之美,我爱闪闪亮
苏州刺绣研究所座落于环秀山庄,这是一座古雅清幽的园子,有繁茂的桂树、翠绿的细竹,有曲折的回廊、流水的假山。最妙的,是不经意间的惊艳,比如转角天井里一株高大的芭蕉,比如走廊尽头一处小巧的露台。说世界顶级的苏绣就在这盆景般的山水间诞生,真是令人信服。
如此温润的背景上,郁晓莹笑着走来,闪亮了人眼———绚丽的花裙,波浪的卷发,描得明丽的五官———洋气地美着,与想象中刺绣工艺师的样子大不相同。而细谈之下,才能发现她骨子里又有点特别的、与这城市气质契合的东西。
郁晓莹说,长在苏州的人是有福的,起码记忆的片段就有些别致。至今,她难忘小时候,温暖的午后,挑着担子的小贩叫卖糖粥、生煎馒头,那是苏州人必备的下午茶点。她记得见婶婶为刺绣厂加工日本和服腰带,那精巧的花纹让她惊艳。她还记得自己穿过一条条白墙黑瓦的小巷,奔去外婆家,每次都会从环秀山庄门口经过。她好奇古香古色的大门里有些什么,视线却被灌木花草与假山挡住,只余无限想象……
这些片断滋养了她对美的感觉、渴求。她从小就爱闪闪亮的东西,拼命收集水晶、玻璃制成的小戒指、小项链。问她,苏绣也闪么?她快乐地回答:仔细瞧,把丝线放在有光的地方,轻轻转一下角度,就有不同的光芒,呈现不同的色泽呢!
1995年,从苏州市工艺美术技工学校刺绣专业毕业后,郁晓莹便兜兜转转,走进了那座引她遐思的园子。她很得意于自己的工作。还在读书时,她曾有机会参观过刺绣研究所。同样绣的是小猫、金鱼,研究所展示的作品上,蓬松的毛感、神气的眼睛,太吸引人了。和她之前在别处看到的不一样,那些粗糙的商品连形都没有,动物的毛就像牙签插在身上。
最让她眼睛挪不开的,是金鱼的尾巴,尾端飘飘忽忽,似有若无。能做出这种效果,全凭丝线的功劳。捏起一根细细的绣线,老师傅伸出指甲,轻轻一划,线被纵向劈开,再劈,再劈,绣线迅速被分成48份,这几乎是蚕宝宝吐的原丝粗细了。这样的丝线,瞧不清,也捏不住,只能用手指肚捻起,屏住气,凭感觉,无声无息穿过针孔,这才开始漫长的刺绣。
真是细巧到极致的活儿呀!郁晓莹笑了:苏绣玩的就是精巧。
苏绣使用的布匹,是特制的,比纱巾还轻薄。见过一幅作品,绣的是只羽翼丰满的鸟儿,五六步之外望去,绣品依托的布几乎看不清,只见鸟儿空灵独秀地立在半空,脱离凡俗的气质令人赞叹。
苏绣使用的丝线,也是特制的,每种颜色都成一个色系。即便是不起眼的灰,也有深浅不一的几十种,送到工艺师手上的线,因此都是大包大包装着,之后要分门别类晾在许多木架上。
苏绣使用的技法,是多年来无数工艺师总结、丰富的。总体来说,针法有二百多种,常用的有几十种。而每种针法里,还有衍生的技法。就像是人类社会众多的语种,每个大语种中,还有区别微妙的小语种。再熟练的工艺师,对于苏绣的技术运用也有限,各人运用的针法、丝理都不同,这就是所谓“术有专功”。
精致的材料、技术,使刺绣的过程也相当“娇贵”———刺绣研究所要求艺术家们一定要在自然光下绣,不然对颜色的把握不准确;一定要注意线的走向,偏一点角度,因为丝线的反光问题,就会呈现不同色泽;一定要保持手部肌肤的光滑,略粗糙的抚摸,就会破坏娇嫩的丝光……
“没人不爱这样的好东西。”爱美爱闪亮的郁晓莹全心投入了这项事业。
缓缓之美,我爱桃花源
郁晓莹性格中有着白羊星座人火爆、强烈的特质,奇怪的是,却可以做这样慢工出细活的工作。要知道,即使是绣一片小小扇面,也需要两个月。她这工作一做十七年,也不过得了二十多幅作品。在效率就是一切的今天,如此缓慢的做事方式,简直让人惊叹。
忍着急躁,放慢步调,会不会觉得憋屈?
郁晓莹又笑了:从事这行以来,最枯燥的时候,莫过于在学校练基本功。就是绣最最简单的长方形,用传统绣法,一排一排上线,比谁线条排列最整齐。之后花样多点,也不过绣片花瓣,依然是比谁线条最齐整、谁边缘最光滑。冗长单调的操练,她却不觉无聊,在自己均匀的呼吸声中,体会着银针上下穿梭、似乎要延续到永恒的节奏感,甚至都有些迷醉了。
之后,她进了刺绣研究所,并不是正式开工,前面两年,又将传统针法全数温习了一遍。
此后,经过任慧闲、顾文霞、张美芳等著名苏绣艺术大师的指点,加上自己刻苦钻研,她根据自己素描功底深厚、喜爱西洋画的特点,在传统苏绣和乱针绣之间,选定了乱针绣的制作。
所谓乱针绣,说白了,和绘画中的素描相似,只是用绣线代替了铅笔画出的线条。为描摹事物,就要一层层去打线条,去渲染。
比如绣风景画中的一片小山头,每层丝线的加法都不同,要捉摸着整体感觉,考虑哪里需要加线条、怎么加、加什么颜色、加多少……全凭工艺师的经验、对各类针法的把握程度。这样,每绣完一层,观感都不同。有的地方,甚至要加五六层刺绣,直至针都顶不进去,针尾把手指顶破,和纳鞋底差不多。
“你看,稍有差池,画面效果就大不同,每一针做上去都有自己的作用。这样的工作怎么会枯燥?”郁晓莹得意地笑了,“我平时性子可急了,走路都风风火火,刺绣起来偏就稳得住。这事儿不能急,急了就早产,前功尽弃。”
焦虑,似乎是快节奏社会中人的普遍情绪,和所有人一样,郁晓莹也会感觉生活的压力———会面对外界的灯红酒绿叹息,会关注股市的起起伏伏,会收到儿子老师发来的、让人紧张的手机短信,会有做不完的烦死人的家务……但是,在她走入刺绣研究所的园子时,这一切,便被沉重的大门关在身后。
那刻,她的眼前、她的世界里只有苏绣。那刺绣是当下,唯一被实实在在捏于手中的。她什么都不用想,只需思考,怎样恰到好处地绣出下一根线条。真单纯,真纯粹!郁晓莹觉得,只有做这样简单的事情,才让人觉到有安全感、力量感,似乎一切都可掌控。于是,心绪沉淀下去,一切回归宁静。
有时,手微酸,她便停下,望向窗外。那里,是看惯了的一片黑瓦的屋顶,屋顶上是一如既往蓝的天,脑海中是一片纯白。这样发呆的时间,往往能持续一阵子,却也不倦。因为,只有在那时,郁晓莹才感觉拨开了尘世的迷雾,走向离自己最近的地方。“这是我心中的桃花源。”爽辣的她难得如此感叹。
个性之美,我爱大想象
苏绣的传统气息,让郁晓莹体会到别样人生,却不能改变她求新求异的冲动。也许,正是这一点,让她的作品显出与众不同。
刺绣研究所的工作异常严谨,在这里,不管你年纪多大,工作多久,永远都是学生的身份,需要不断磨练、学习;需要每天接受老师傅的巡视、指导;活儿完成了,还要面对大伙儿的评判,之后是大师不断地指正、修改。郁晓莹算得上是所里骨干了,却也是近三十岁,才第一次独立完成一幅比较大的作品。那次,她接受了唯一的、也是最惨痛的一次教训。
那是一个叫《六骏图》的作品,内容是六匹神采奕奕的白马。第一次绣白色的动物,郁晓莹没什么经验,就照着原作,观察到什么颜色,就直接绣上什么颜色的丝线。旁边的老师傅提醒:绣淡色的动物,一定要用白色丝线打底,之后再上别的色。郁晓莹一贯想法就和别人不同,偏巧,因为有灵气,之前每次冒险,也都成功了,这回依然我行我素。不料,绣出的白马颜色感觉特别脏、乱,不得不半途废弃。
她没有否定自己的创新,但承认了自己的莽撞。这次失败后,她并不就此畏缩,不敢实施新创意。但她在操作上更细腻了。比如,针脚更短些,用色更淡些,线条排列更细些,总之,动作都收敛一些,宁愿多绣几层,多花点功夫,一点一点地验证效果。
郁晓莹最优秀的作品之一,是与姐妹们共同绣制的一幅《彩墨荷塘》,作为外交部礼品远送欧洲,被驻欧洲使馆收藏,使馆还专门发来谢电。原作是我国著名画家袁运甫先生绘制的。画风华丽浓艳,气象辉煌,彩墨数点却荷摇万支。郁晓莹很喜欢这幅画儿,因为爱一切亮丽事物的她就青睐“立体感强,色彩浓郁”的艺术品。
绣制这幅作品时,她很是花了一番心思:对主体部分的荷花花瓣,她采用细密均匀传统的平绣,以突出其光洁;对花蕊,用小圆圈状的打籽针、松子针表现立体;而远远近近、大大小小的荷叶,以及背景中的流水则用长短不一、方向交叉的乱针绣,不让丝光跑出来,以免喧宾夺主。这样一来,画面主体突出、虚实结合,逼似原画意境,又有刺绣工艺的独特魅力。
还比如,她独自绣的《故山夕照》。画面前面有一丛树。一般工艺师会用短针做小交叉,体现灌木一丛丛的感觉。郁晓莹却一改习惯做法,用一个个小线结表现灌木。如此,明暗变化愈加微妙,颜色层次也更加丰富,而最重要的,是那一个个小点,很闪,很亮,闪得郁晓莹心花怒放。后来,这幅作品得到了“2010年艺博杯工艺美术精品大赛”的银奖。
郁晓莹说,实践越多,就越感到,一幅作品变画为绣的不易,对绣者来说,首先在思维上要有一个飞跃———从感性到更感性,从想象到大想象。
如今郁晓莹,不仅是苏州刺绣研究所的中坚力量,是2010年苏州市妇女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代表,也是在《新华日报》、《江苏经济报》、《苏州日报》等多家省市媒体、国内外各大网站上被相继报道的优秀工艺师。然而,一切浮名无法让人幸福,只有全心全意于苏绣,在其中投入所有的情感、想象、创意,郁晓莹才如此快乐着。
 分享
分享






